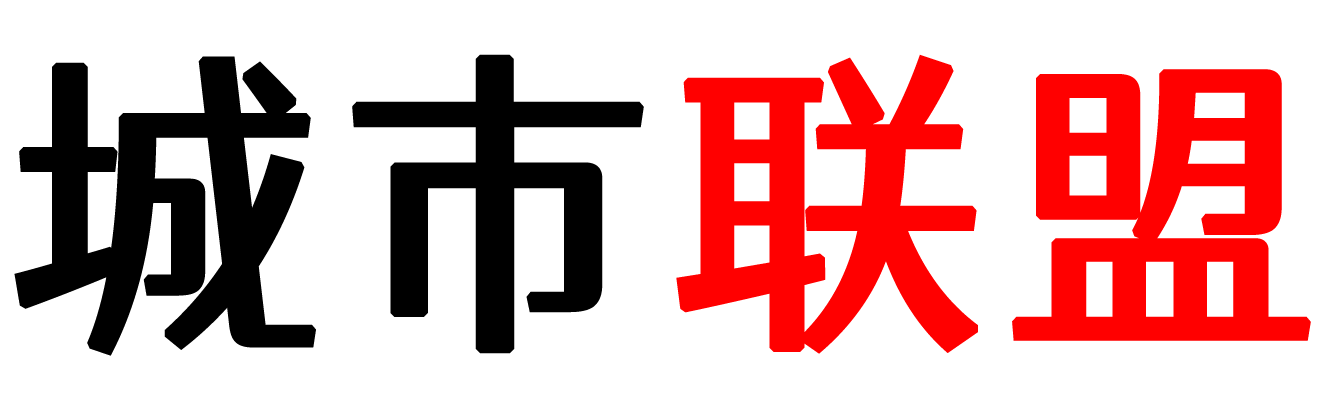新中国的生死之战: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
- 2016-01-16 03:31:02
- 2809
一、基本思路
由于挽救了危在旦夕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朝鲜,以区别于韩国或南朝鲜),并支持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抗美援朝的国际意义历来为国内外所公认nyq。然而这场战争究竟是否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几十年来却争议不绝。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国内以高岗、林彪等中央领导人为代表的一派意见就坚决反对出兵援朝,在他们看来:中国历经数十年战乱的破坏,需要时间来恢复经济;“联合国军”陆、海、空三军的装备水平占绝对优势,我军参战必须有起码三、四倍于对方(即绝对的数量优势---作者注)的装甲兵和炮兵以及空中掩护,而这些条件我国根本不具备;朝鲜不过相当于中国一个省那么大,让它亡几年无关大局。所以出兵援朝是惹祸上门,引火烧身。林彪为此而称病去苏联疗养,推托志愿军司令员的职务任命。他们认为此战中国可打可不打,主要顾虑打不嬴而不一定不该打,因而在志愿军旗开得胜后便无声无息了。
九十年代以来,这个话题再度活跃起来。在七、八年前,本人曾亲自听到访华的美国学者发表一种“抗美援朝得不偿失论”,其中有一条近似三段论的基本思路:美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准备作出外交承认,可惜没有得到中方的及时回应;美国干涉朝鲜战争旨在解决朝鲜问题,对中国仍然没有敌意;假如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当观众的话,完全可以与美国发展关系,抓住对外开放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机遇。所以,为挽救朝鲜而进行抗美援朝得不偿失,给中国带来一场长期的灾难。一言以毕之,“为中国着想”,抗美援朝无论胜负都不值得一打。主客双方就此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记得客方质问:“美国一统朝鲜有什么不好?”主方一位青年教师用英语反问:“你们干脆打过鸭绿江,连中国一齐统一,岂不更好?!”客方无言以对。当时,在场的东道主们觉得双方的立场、观点不同不足为奇,因而不大介意,只不过反感对方有些混不讲理的作风。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的观点在国际上颇有市场,而且逐渐开始进入国内。在近两年的私下接触中,我多次遇到不同职业的人士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怀疑抗美援朝是否符合国家利益。这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要知道对于中美双方来说,朝鲜战争的经验都确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冲突反应模式,半个世纪以来始终牵动着现实的安全利益。而半个世纪以来不只一次出现争议,表明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科索沃危机、尤其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受轰炸以来,国内群情激忿,上述疑问也突然消失 。应该说,群众的热忱提供了一种有利的气氛,然而真正服人还离不开理性思考。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一度隐没的问题可能再次浮出水面,给国家的安全决策造成障碍。
所以本文刻意尝试探讨“保家卫国”的内涵,回应有关的争议,从国家安全的视角评价抗美援朝。侧重点置于以前没有充分展开的一个问题:让美国在朝鲜为所欲为,对于我国的安全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相信,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对抗美援朝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文章的结构同样以三段论式为基础,我认为无论观点如何,这样的布局都基本对应特定历史事件自身的三个主要演化阶段,即朝鲜战争及其前因后果。因此本文围绕我国的安全利益,将内容主要分为“战前的美国对华政策”、“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参战的潜在威胁”三大部分,分别考察朝鲜战争的历史根源、美国参战行动的意图和性质、我国安全所面临的危险,最后就抗美援朝的评价问题,以适当的方法作出自己的结论。中国和美国是朝鲜战场上的两个主角,两国的利益及政策互动自然成为战争及本文的主线。
二、战前的美国对华政策
正确解读战前的美国对华政策──朝鲜战争的主要背景,对于判断这场战争的性质及其后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众所周知,从我们建国到朝鲜内战爆发的9个月期间,美国始终没有给予外交承认。然而近年来开放的许多信息又显示,美国政府在当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动向,诸如:在解放战争末期,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驻华使馆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后,美国使馆仍留在南京,等待与新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美国政府向我国政府表示,愿意提供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曾考虑过承认中国,并于1950年1月5日同一天先后声明,继《波茨坦公告》之后再次确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宣布不准备武力干预中国局势……等等。如何解释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呢?国内外众说纷纭。我认为美国政府的某些积极动向作为史实得到多方的援用,可以姑且相信其可靠性,然而它们全属于政府的表面姿态,远不足以说明政策的实际含义。须知欧美的教科书至今仍常用一句名言作为外交的非正式定义──“到海外为祖国的利益而撒谎”,因而把保密当作外交的第一要诀。平心而论,我认为那句名言未免夸张,但它也多少符合外交领域的一个普遍特征──虚虚实实。因此本文遵循政策分析的一般方法,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对象、利益基础和目标由里及表地逐一推敲,力求揭示钱币的另一面。
1、美国对华政策的对象──中国对美政策
新中国诞生于冷战年代,包括对美政策在内的整个中国对外政策体系受到这种国际大环境的有力制约 。当时两大阵营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对抗,都把意识形态因素当作对外交往的首要原则,我国也不例外。中央政府相应地制订了对外交往的三大基本方针:一、“另起炉灶”,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的新基础上与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二、“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将发展与“兄弟”国家的关系置于首位;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先清除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势力和影响,不急于同它们建交。三大基本方针在执行过程中走得更远,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界人士大部分被轰走,与之打过交道的中国人则沾上了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嫌疑。在三大基本方针所指导的对外政策体系里,对苏和对美政策形成突出的两极。1950年2月签订《中苏互助友好同盟条约》后,两国正式结盟。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前国民政府的主要国际支持者和资本主义阵营的领袖则首当其冲,成为反西方政策的头号目标。
上述不利于发展中美关系的环境因素无需否认,不过应该加以分析而不能满足于单纯的描述。从道义上讲,一个受了西方列强一百多年摧残的民族作出某些过激反应在所难免,无可厚非。从历史环境看,同苏联结盟也符合当时的民族利益。我们家底太薄,亟需外国援助来启动工业化和防务建设,包括大规模的技术转让,以及大量的武器装备以对付频繁袭击大陆并准备反攻的国民党、迟早要重新武装的日本、驻越法军等等,且不论占领日本的美军。惟有发展模式与我相同的苏联满足了这个最低要求,帮助我们在十年内就为自己的工业体系和防务体系(包括核武器)打下了基础。反之,强大的近邻苏联一旦闹翻,则比远邻美国更危险。从一般政治和地缘政治两个角度来看,中国都是冷战“边界”上的唯一大国,具有改变世界权力平衡的关键作用,从而陷入两大阵营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之中,成了它们的必争之地。假如我们不顾自身的处境和条件而盲目模仿瑞士、印度、南斯拉夫等中立国,轻则丧失任何一方的援助,重则腹背受敌,遭到双方的挤压乃至合击。例如在六十年代,美苏都曾制订了对华核打击的计划,甚至出现过两超合谋对我实施核轰炸的惊险动向。今日南斯拉夫的悲剧证明,中立有时也会“挡道”得罪人的 。以我们在建国初期的综合实力而论,象六十年代那样同时对抗两超、象七十年代那样联美抗苏或者象改革开放后那样完全独立自主,都为时过早,而只能象抗战时期那样集中力量(包括盟国的联合力量)对付主要威胁。
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成功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我们从来不象东德、捷克之类卫星国那样完全听命于苏联,我方实际上不存在与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实质性障隘。1950年初,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英国、荷兰等北欧和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承认了中国,经过或长或短的谈判后分别建立了(包括代办级在内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历来极其重视中美关系,1949年6月建国前夕还邀请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访,是美国政府未予接受。我方从不存在拒绝承认美国的问题,从未关死两国交往的大门。从我们建国到朝鲜战争之间的9个月内,只要美国真有诚意,任何它人都不足以阻止它承认中国。所以不管美国政府如何辩白,两国关系中主要的实质性障碍只能到他们自己身上去找。
2、美国对华政策的利益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仍坚持维护“在华利益”,即在华特权。艾奇逊国务卿曾代表美国政府为承认中国而提出“三项准则”:“一、该政府事实上控制了领土和国家机构并能维持公共秩序;二、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在国际上的义务;三、该政府的统治为其人民所普遍默认”。其中第一、三两条只要双方愿意,就可以灵活解释,达成共识。关键在于第二条“准则”中“国际义务”的概念,在当时包括以前各届中国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允许它们在中国享受一系列治外法权,其中也有美国的一份“在华利益”,它们纯属强加给国际社会的帝国主义“惯例”。而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有掠夺性条约,与各国建立平等的新关系。在这方面,双方的不同原则直接冲突,没有妥协的余地。
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的偏执不在我们之下,对国家关系的影响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与它资本主义领头羊的身份有关,而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美国意识形态“一致性”的政治传统。在英、法、荷等西方民主国家,除法西斯分子以外,持其他信仰的人都可以合法地表达见解 。唯独美国仅能听到资本主义的声音,只不过有不同的调门,即尊重“异端”而仇视“异教”,对内宽容而对外偏狭,思想统一的程度甚至超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当然美国不是法西斯,还不至于以恐怖手段镇压不同政见,而是建立一种外松内紧的控制机制。宪法承认言论自由,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极端”事实上无法公开发言与活动,此类移民则不得入境。出于内政的需要,美国在国际上一向不愿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近两年来,克林顿政府仍反复强调要建立一个整齐划一而不是千差万别的国际社会。外国人往往不相信,世界上成分最复杂、个人自由最突出的社会,怎么会推行半专制政治?其实两者恰恰彼此平衡,成分复杂的社会往往结构脆弱,具有巨大的离心力和潜在的爆炸性,反而必须保持起码的“一致性”。由于美国只经历过一种意识形态,这个民族在政治上极其无知而武断,其他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都近乎原罪。无论如何,意识形态“一致性”早已成为他们不可侵犯的国家利益。所以在这个共产主义最不成气候的国度,反共态度却狂热得出奇,仿佛唐吉柯德在与风车搏斗。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会里的保守派就为支持半资本主义的台湾而向杜鲁门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此外不能忽略,苏联与美中两国都有决定性的利害关系,成了中美利益互动中一个关键性的变量。两超在整个冷战时期始终水火不相容,制度之争和国家利益之争在其中紧密交织,否则无法解释苏联解体后,美国为什么还要通过北约东括排挤资本主义的俄罗斯。由于两超于四十年代先后掌握了核武器,双方的较量已经开始具备生死搏斗的意义,压倒并支配了所有其他利益。辽阔的幅员和敏感的战略位置,使我国对美苏双方的力量消长作用非轻,心理上的影响则更大。而近代以来,国力的一落千丈和历届旧政府的腐败无能又令人侧目,抗美援朝前夕,麦克阿瑟将军的狂妄冒进和斯大林元帅的悲观退缩反映出一般国际人士对中国人的轻视。因此两超均不愿理解、更谈不上尊重我们的民族利益和独立自主的意志,而以非此即彼、非友即敌的两分法看待中国的一举一动。这就形成了潜在的利益冲突,随着我们逐步倒向苏联,得罪美国是不可避免的历 史 网。